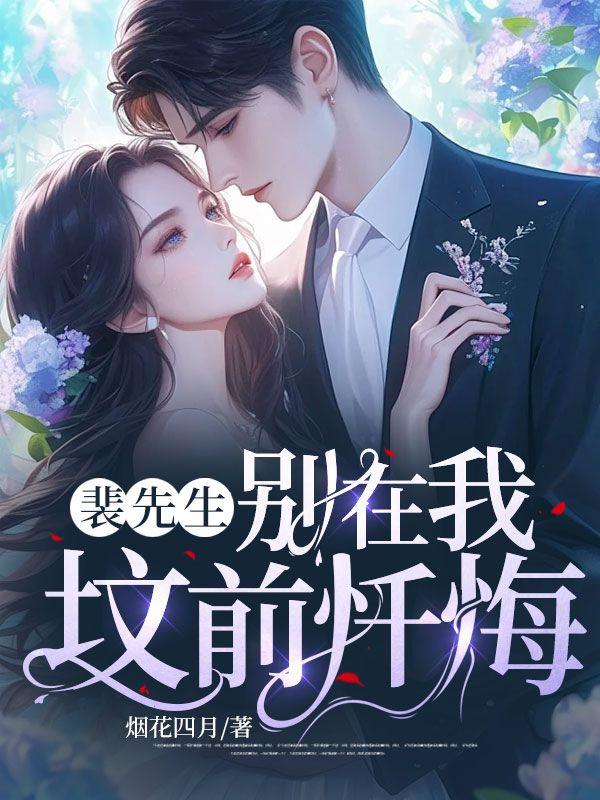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生活系神豪 > 第323章 地中海的抉择(第1页)
第323章 地中海的抉择(第1页)
第二天早上,李言从迈阿密飞往欧洲。
这次他选择了法航的头等舱,从迈阿密经巴黎转机回尼斯。
总飞行时间约十二小时。
在机场候机的时候,他给沈文打了个电话。
“摩纳哥那边的房产什么。。。
夜雨落进昆明的巷口时,陈浩正蹲在一家老茶馆后院的青石板上。雨水顺着屋檐滴下,在他头顶搭出一片弧形的寂静。他没撑伞,也没穿鞋,脚底贴着那块被百年茶渍浸透的石头,像在等一个迟到的回音。
这块地砖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导震系统。它没有编码,没有信号协议,甚至不在光语社当年绘制的城市共振图谱里。但它有记忆??不是电子记录的那种,而是更原始、更深沉的东西:一种由无数次擦拭、踩踏、跪拜与低语层层堆叠而成的“场”。
三天前,他在大理收到一条匿名信息,只有一串经纬度坐标和四个字:“听一听她。”
他本可以不理。自从解散光语社、焚毁资料后,他已经学会对一切可疑线索保持沉默。可那天夜里,他梦见了小满穿着那双发白的布鞋,站在一片干裂的河床上,轻轻敲击地面,三短一长。
醒来时,他的掌心发烫。
于是他来了。
此刻,雨声渐歇,城市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安静。陈浩闭眼,调整呼吸,让心跳缓缓下沉,逼近那个熟悉的8。3Hz。他知道,真正的倾听从不是耳朵的事,而是全身细胞的共振准备。
忽然,右脚外侧的地缝中传来一丝异样。
不是震动,也不是声音,而是一种“缺失”??仿佛某段频率本该存在,却被硬生生剜去,留下一个空洞的凹陷。就像一首歌正唱到副歌,却被人按下静音键。
他皱眉,指尖轻抚石面裂缝。那里积着雨水,水纹微颤,却不散开,反而聚成极细的一线,沿着某种看不见的轨迹缓缓移动。
这不对劲。
自然的震波会扩散,不会定向流动。除非……有人为引导。
他迅速从背包取出一枚微型谐波探测针??这是他在纳西村自制的土设备,用废弃手机震动马达改装而成,灵敏度远不如专业仪器,但胜在不联网、无信号、无法追踪。
将探针插入缝隙,连接耳机。
起初只有杂音:地下水渗流、远处地铁穿行、建筑钢筋热胀冷缩的呻吟。但当探针深入两厘米后,一段极其微弱的脉冲浮现出来。
**7。83Hz**。
舒曼共振基频。
可紧接着,第二波叠加其上??**8。3Hz**,小满最常使用的回应频率。
但第三波变了。
不再是柔和的波动,而是锯齿状的扫描波,带着强烈的解析意图,像是某种程序正在逆向拆解这段共鸣的本质结构。
陈浩猛地拔出探针。
又是“ProjectEcho”。
他们不仅没停手,反而追到了这里。
他抬头环顾四周。这座茶馆建于民国初年,曾是马帮歇脚之地,传说每一块地板都听过生死诀别。如今虽翻修多次,但主厅仍保留原木结构,据说是为了“留住茶气”。可现在看来,或许真正被留下的,是另一种东西。
他起身,赤脚走向主屋。木地板吱呀作响,每一步都像踩在旧时光的神经末梢。他没有惊动店主,只是默默绕到供奉土地神的小龛前,跪下,双手合十,再次敲出三短一长的节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