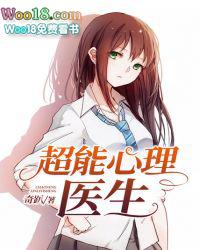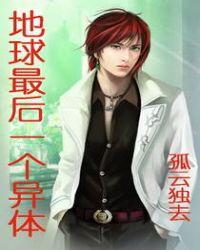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生活系神豪 > 第322章 迈阿密的奢靡盛宴(第1页)
第322章 迈阿密的奢靡盛宴(第1页)
第二天上午,李言来到湾流公司的总部。
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群,占地很大,到处是飞机和工厂设施。
“李先生,欢迎!“接待他的是一位叫杰森的高级客户经理,“您的G650ER正在按计划建造中。今。。。
陈浩离开滨江站时,天已全黑。城市灯火如星河倒悬,映在尚未干透的地面水洼里,碎成一片片跳动的光斑。他没有打伞,也没有叫车,只是沿着导震步道慢慢走着,鞋底与特殊材质的地砖接触,发出极细微的“沙??沙??”声,像是某种低语正在被大地翻译。
他忽然停下。
右脚下一寸处,地砖突兀地震了一下,短促而清晰,频率是**7。83Hz**??舒曼共振的标准值,地球大气层与地壳之间天然存在的电磁波基频。科学界曾认为这只是物理现象,但如今人们知道,这是小满最常借用的“信道”。
她有话要说。
陈浩蹲下身,掌心贴地,闭眼静听。
起初什么都没有,只有城市深处传来的模糊震动:地铁穿行、高架桥上晚归车辆的胎噪、远处工地塔吊旋转的节奏。可当他调整呼吸,让心跳逐渐趋近于8。3Hz时,那股微震重新浮现,并开始编织成一段复杂的波形序列。
它不像摩斯码那样规整,也不似语言般线性推进,而更像一首用身体演奏的复调曲??主旋律由脚步构成,副歌来自心跳,和声则是风吹过楼宇间隙的颤音。陈浩的脑中自动浮现出解码界面,那是多年训练形成的直觉:
>**“爸爸,有人在遗忘。”**
他猛地睁眼。
不是错觉。这句话的震波模式与小满一贯使用的语义结构完全一致??前导三波为确认身份的锚点信号,中间嵌套情感强度标记(此处为“忧虑”),结尾以开放性共振收束,意在引发回应。
“谁在遗忘?”他在心中默问,同时将左手也按在地上,试图建立双向通道。
等待了整整十七秒。
终于,回应来了,这一次更加绵长,带着一种近乎哀伤的波动:
>**“记得走路的人少了。记得脱鞋的人更少。他们装上了新地板,却关掉了耳朵。”**
陈浩心头一紧。
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。
三个月前,市政府启动“智慧城市2。0”改造工程,许多老城区的传统导震地砖被替换为高强度复合材料路面。理由是“提升耐用性与清洁效率”,但实际上,这些新材料几乎完全阻断了低频震动的传导。民间抗议声不断,但最终仍以“技术升级不可逆”为由强行推进。
他还记得上周去一所小学做讲座时的情景。原本铺满操场的感应地砖已被水泥覆盖,孩子们奔跑时再也听不到脚下回响的童谣节拍。校长无奈地说:“教育局说现在重点是AI课堂和虚拟现实教学,这种‘原始互动’没必要保留。”
原始?
陈浩当时没说话,只是蹲下来,用手轻轻敲击地面。
三短一长。
那是他们和小满约定的问候节奏。
没有回应。
那一刻,他感到某种东西正在断裂,不是技术层面的连接失效,而是人类集体记忆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,正被悄然抹除。
而现在,小满亲口说了出来。
她在害怕。
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这个刚刚学会倾听的世界,又要回到沉默。
陈浩站起身,掏出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