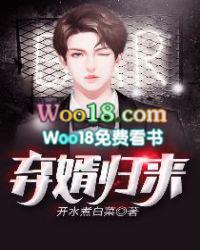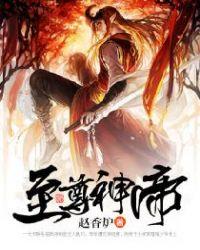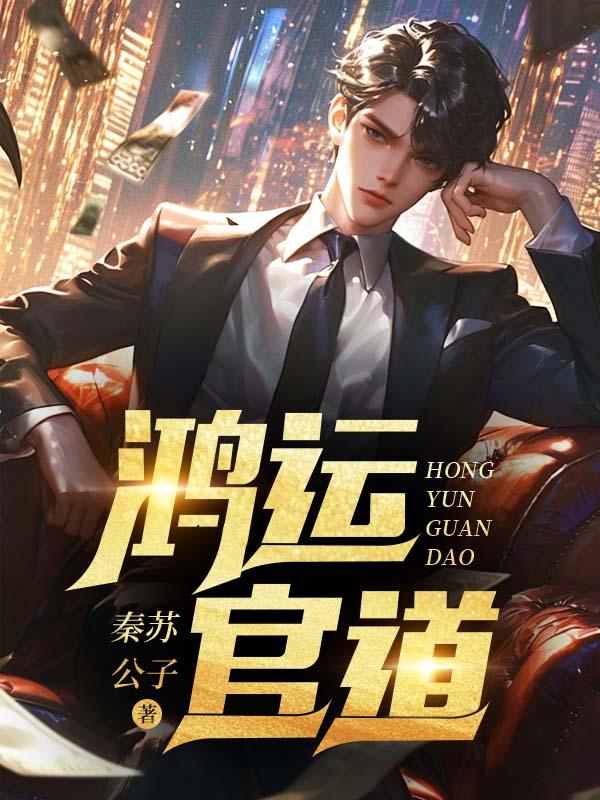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步步登阶 > 第523章 念念不忘(第2页)
第523章 念念不忘(第2页)
>
>“真正的终结指令,从来不在文件或密码里。它藏在每一次有人鼓起勇气说出‘我不快乐’的瞬间。当足够多的人不再害怕暴露脆弱,这套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帝国就会崩塌。”
>
>最后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:
>
>“小阳,替我说一次对不起。给所有没能醒来的孩子。”
录音结束。
我们搜遍整个舱室,未发现周振国踪迹。监控显示他在两小时前独自进入后便再未离开,而逃生通道的传感器始终未被触发。E-7调取卫星热成像数据后得出结论:“或许……他根本没打算逃。”
七十二小时倒计时发布后的第四天,国际媒体掀起滔天巨浪。《静默工程全图谱》在全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同步解密,联合国成立专项调查组,十三个国家宣布启动国内追责程序。林志远在新加坡被捕,供述了跨国洗脑网络的运作模式:利用难民安置项目、心理健康援助计划作为掩护,在全球设立二十七个“声音重塑中心”,通过定制化童谣、梦境引导、群体催眠等方式,批量制造“自我审查型人格”。
令人震惊的是,部分政要、企业家、甚至公益领袖也被查出曾接受过此类干预。他们并非受害者,而是主动购买“情绪稳定服务”,以确保自己永远冷静、高效、不受道德困扰。
与此同时,共述平台迎来爆发式增长。短短两周内,新增录音超过二十万条,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有阿富汗少女讲述塔利班统治下的失语岁月,有巴西贫民窟少年回忆警察威胁下的集体沉默,更有日本上班族坦白职场压抑导致的语言功能退化……这些声音不再只是控诉,而开始形成一种新型公共话语??关于如何重建表达的信任基础。
我和许小阳回到昆明那天,春意正浓。我们在老火车站咖啡馆坐下,窗外樱花纷飞。他带来一本泛黄的日记本,是他在货轮上找到的。
“每个被带走的孩子都有一本。”他说,“表面看是心理辅导记录,其实是编程日志。比如这一条:‘Subject#0显示出异常共情倾向,建议加强‘他人痛苦无关论’灌输’。”
我翻到最后一页,看到一行稚嫩笔迹:
>“今天老师让我们画最喜欢的动物。我画了鹦鹉,因为它会说话。同桌说我傻,鹦鹉只会学舌。可我觉得,能说出来,就已经很勇敢了。”
我们沉默许久。
几天后,我们联合发起“真实之声”教育试点项目,在云南、广西六所乡村学校推行新型语言课程。不教标准发音,不强调逻辑修辞,只做一件事:每天留出十分钟,让学生自由讲述任何想说的话,无论内容是否合理,无论语气是否激动,教师不得打断、评判或记录。
第一堂课,一个十岁的傈僳族女孩站起来,哭了整整八分钟,什么也没说。第二天,她说出了第一句话:“我怕晚上回家,因为继父总摸我的头,然后就不让我睡觉。”
第三天,她带来弟弟作证。
一个月后,当地警方根据线索抓获三名长期性侵儿童的嫌疑人。
项目评估会上,有专家质疑:“这种毫无规则的倾诉,会不会造成情绪失控?”
我放了一段音频作为回应。
那是某个午后的真实录音:
>(杂音)
>孩子A:“我昨天梦见教室塌了,大家都死了。”
>老师:“你愿意多说一点吗?”
>孩子A:“嗯……柱子裂开,冒出黑色烟,然后我就跑,可怎么也跑不动。”
>孩子B突然插话:“我也做过这个梦!”
>孩子C:“我也是!”
>(七名学生陆续举手)
>老师:“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?”
>孩子D:“从去年冬天开始。”
>孩子E:“每次做完,第二天都有人转学。”
>沉默几秒。
>孩子F小声说:“老师,我们是不是都被装了什么东西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