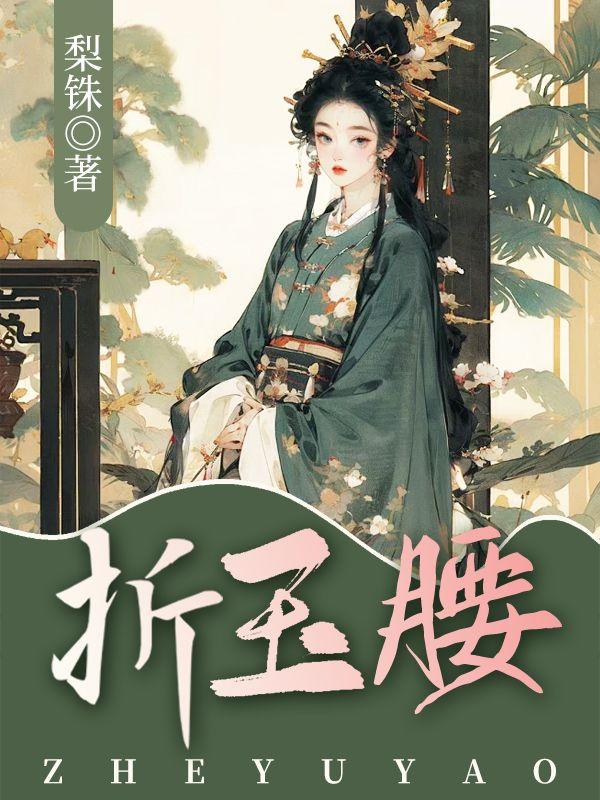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二婚嫁京圈大佬,渣前夫疯了 > 第1491章 霍长亭打个赌吧(第2页)
第1491章 霍长亭打个赌吧(第2页)
因为她听见了回音。
不是来自空气,也不是风振,而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一丝共鸣,如同沉睡的神经末梢被轻轻唤醒。她猛地低头看向那枚残缺的铃舌,只见它竟微微颤动了一下,随即归于平静。
“你听到了吗?”她抓住晨的手。
晨睁开眼,脸上带着笑意:“听到了。它说……欢迎回家。”
林知遥的眼泪无声滑落。
那一刻她终于明白,真正的共感从未消失。它不在机器里,不在协议中,也不依赖任何技术手段。它是血脉之间的共振,是爱与痛交织出的频率,是当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开口时,世界为之让路的那一秒静默。
他们离开时,雨已停。天边裂开一道缝隙,阳光斜斜洒下,照在湿漉漉的铜铃上,折射出七彩光芒。
当晚,晨把这段录音命名为《雨中的回声》,并决定收录进他即将出版的第二本书《听不见的孩子》中。
书稿完成后,他请林知遥写一篇序言。
她思索良久,写下:
>“他曾是一个无法感知温度的孩子,连拥抱都会让他颤抖。
>可如今,他能听见雨滴落在叶面的千种情绪,能从陌生人的脚步声里分辨出疲惫或喜悦。
>他不是被治愈的病人,他是重新定义‘听见’意义的人。
>而我有幸,成为他第一个听众。”
出版社收到书稿后大为震动,主动提出全国巡讲计划。商景予得知消息,亲自联系团队,安排全程安保与心理支持小组随行。
“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。”他在电话里对林知遥说,“这是人类情感重建的里程碑。”
林知遥笑了笑,没多说什么。
她知道商景予一直关注着晨的成长。这位京圈最冷峻的大佬,曾在某个深夜独自驱车百里,只为送来一批国外定制的情绪识别训练卡片;也曾默默资助“光之桥”计划的偏远站点建设,不留名姓。
但她更清楚,他对他们的在意,早已超越了科研兴趣。
那是一种深藏的愧疚与救赎。
因为二十年前,正是商氏集团前身参与了ECHO项目的资金支持。尽管他当时尚未掌权,且极力反对人体实验,但在权力倾轧中未能阻止悲剧发生。母亲的死亡、林知遥的被迫觉醒、晨作为L-7号实验体所承受的一切……这些血债,哪怕与他无直接关联,他也始终背负着。
直到遇见她们。
直到看见晨在他的书房里,毫不畏惧地爬上高脚椅,指着书架上的心理学典籍说:“这本书的名字好长啊,我能借回去抄一遍吗?”
那一刻,商景予眼眶微红。
他低声说:“不用借,送你。以后这里所有的书,你想看多少,拿多少。”
后来,晨真的每周都去一次商宅。不是为了见他,而是为了蹭书、蹭空调、蹭免费点心。管家笑称:“小少爷把这儿当成自习室了。”
商景予从不恼,反而每天提前吩咐厨房准备孩子最爱吃的红豆糕。
有一次,林知遥陪晨去取书,无意间在走廊听到他打电话。
“……我知道当初签那份协议的是我爸,不是我。但责任不能一代代推下去。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,都是在还债。”
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什么,他冷笑了一声:“你觉得匿名捐款就够了?看看那些孩子的眼神!他们需要的不是钱,是有人敢站出来说??对不起,是我们错了。”
林知遥静静站着,没有出声。
她曾以为自己恨过这个家族,恨过那些西装革履却冷漠无情的决策者。可此刻,她忽然觉得,或许真正的强大,不是永不犯错,而是敢于直面错误,并用余生去弥补。
回家路上,晨问她:“沈姨说,有些大人一辈子都说不出‘对不起’这三个字,是真的吗?”
林知遥点头:“是真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