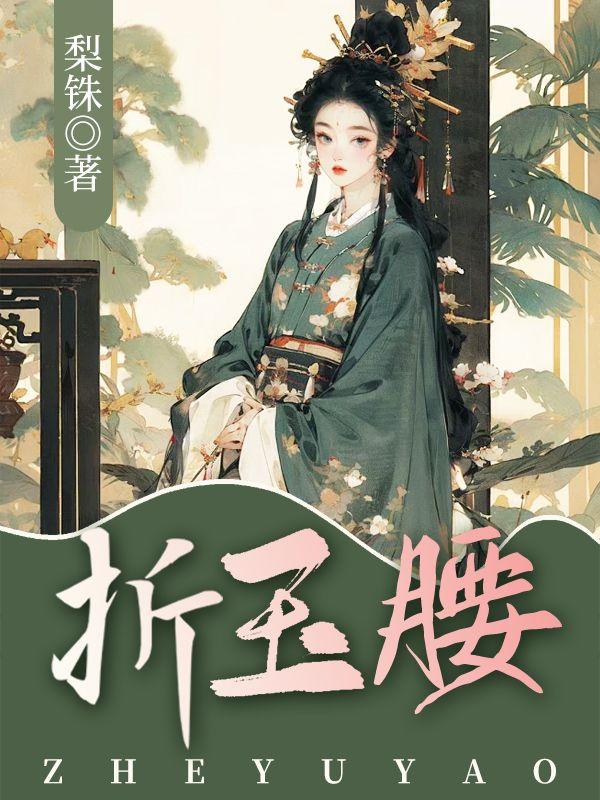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得罪资本后,我的歌越唱越红 > 第二百九十五章 又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亮剑版权上交国家(第1页)
第二百九十五章 又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亮剑版权上交国家(第1页)
12月初,冬日的夜晚,天空中不知何时开始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,夜色下的城市逐渐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,站在高层落地窗的视角看去,一览无余,还真的是非常的壮观。
挂断了跟刘瑜的电话之后,沈铭恩紧接着。。。
黑龙江的冬天来得比预报早了三天。沈铭恩的车刚驶过同江,乌苏里江两岸已结出薄冰,像一层层撕不破的玻璃纸,在晨光下泛着青灰。他连夜赶路,抵达抚远时,天还未亮,街灯在寒雾中晕出一圈圈昏黄的光晕,仿佛整座小城正从漫长的梦里缓缓醒来。
联系好的家属住在江边一处老旧平房,门口挂着褪色的鱼干和一串风铃,是用旧渔网铁环串成的,风吹过时发出低沉而断续的响,像是某种无人能解的暗语。开门的是老人的小儿子,五十多岁,脸上刻着常年与风雪搏斗的沟壑。他沉默地打量沈铭恩片刻,才侧身让进屋。
屋里烧着土炕,热气混着药味、霉味和陈年木头的气息。九十四岁的老渔民伏在枕上,呼吸微弱,眼窝深陷,嘴唇干裂如冻土龟裂。床头放着一支桦皮裹制的短笛,据说是赫哲族“伊玛堪”说唱艺人传下的法器,如今早已不再吹奏,只作为镇宅之物供奉。
“他三个月没说话了。”儿子低声说,“医生说,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。”
沈铭恩点头,没多问。他脱鞋上炕,轻轻将录音设备摆好,又从包里取出一块毛毡垫在老人颈下。然后,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音响,播放了一段音频??那是他在黎寨录下的《塘边等风》,未经任何处理的原声。
房间里很静。只有电流轻微的嘶鸣,和文阿公那断续的鼻箫声缓缓流淌。
奇迹发生在第三分钟。老人的眼皮忽然颤动了一下,接着,喉间发出一声极轻的“嗯”。
儿子猛地抬头,眼中闪过惊疑。
沈铭恩屏息,调低音量,改播一段更古老的赫哲族摇篮曲,是他从省非遗档案馆翻出来的1957年田野录音。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,老人的手指竟微微蜷起,像抓住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“爸……?”儿子试探着唤了一声。
老人没有睁眼,但嘴唇开始缓慢地开合,仿佛在默念一首歌。
沈铭恩立刻按下录音键,同时掏出笔记本,逐字记下那模糊不清的音节。他听不出完整词句,却辨出了旋律轮廓??那是典型的赫哲调式,五声音阶中夹杂滑音与喉颤,如同江面浮冰相撞时的震颤。
接下来的两天,他几乎寸步不离守在炕边。每天清晨六点,他都会播放一段不同的传统渔歌,有时是《打鱼的人哪莫回头》,有时是《乌苏里船歌》的老腔版本。每一次,老人都会有微弱反应,有时是手指轻敲床沿打拍子,有时是喉咙里哼出半句残腔。
第三天夜里,暴风雪突至。窗外狂风呼啸,屋顶的铁皮被掀得哗啦作响,整个屋子像在怒涛中颠簸的小舟。就在这风雨交加的凌晨两点,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。
浑浊,却清明。
他望向沈铭恩,嘴唇微动:“……你……听……过……捕鱼……歌吗?”
声音细若游丝,却像一道闪电劈开长夜。
沈铭恩俯身靠近:“我想听,您能唱给我吗?”
老人闭上眼,许久,缓缓吸了一口气。那一口气拉得极长,仿佛从肺腑深处榨出最后一丝生命力。然后,他开口了。
没有伴奏,没有节奏,甚至不成段落。
但他唱了。
歌声苍老、破碎、断断续续,像冰层下艰难奔涌的暗流。每一个音都带着喘息与颤抖,可那旋律却异常清晰??那是赫哲人世代相传的《捕鱼歌》,记录着春汛开江、夏网撒滩、秋鱼归仓、冬冰封河的四季轮回。歌词是古语,沈铭恩只能听懂片段:“白露降,网绳紧;大马哈,逆流上……江神赐我三尺刃,剖开寒水取金鳞……”
他一边录,一边流泪。不是因为悲,而是震撼??这声音太真实了,真实到近乎疼痛。它不属于舞台,不属于流量,不属于任何标签化的“非遗展示”,它是生命本身在燃烧最后的热量,只为把一段记忆传递出去。
唱到第三节时,老人突然停住,剧烈咳嗽起来。儿子急忙端来热水,却被他轻轻推开。他盯着沈铭恩,眼神忽然变得执拗:“你要……带走它……不然……就没了。”
“我带走了。”沈铭恩握紧他的手,“但我不会让它变成展品。我会让它继续活着。”
老人点点头,像是放下千斤重担。他闭上眼,不再言语,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
那一晚,沈铭恩彻夜未眠。他反复回放录音,逐帧分析音高与节奏,试图还原完整的结构。但他很快意识到:这首《捕鱼歌》本就没有“完整”的版本。它本就是口耳相传、因人而异的流动体。真正的价值不在“准确”,而在“存在”??在于一个九十四岁的灵魂,在生命尽头仍选择开口,把名字刻进民族的血脉。
他决定不做修复,不做拼接,不做任何美化。他要原原本本地上传,连同那一声声咳嗽、喘息、沉默的间隙,全都保留。
第四天清晨,雪停了。阳光刺破云层,洒在乌苏里江上,冰面反射出银白色的光,宛如一条巨龙盘卧于大地。沈铭恩穿上厚棉衣,背起设备,对家属说:“我想去江上录一段环境音。”
对方犹豫:“太危险了,冰还没稳。”
“我就站在岸边。”
他独自走向江心方向,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走到一处冰裂较宽的地方,他停下,打开麦克风,对着冰层轻声说:“老哥,我来了。你的歌,我带走了。但你放心,它不会死。”
然后,他蹲下身,将麦克风贴近冰面,开始录制。
寒风掠过耳际,冰层深处传来细微的“咔咔”声,像是地下水脉仍在流动,又像某种古老的心跳。他忽然想起日记里的那句话:“只要有人肯凿开一个窟窿,俯身倾听,就能听见整个民族的心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