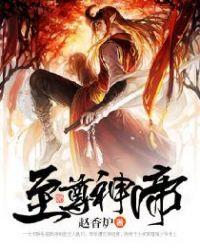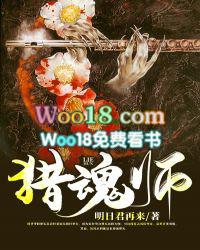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四合院:一人纵横 > 第2095章 赤红魔晓30(第3页)
第2095章 赤红魔晓30(第3页)
静止过后,元初芥子开始“无显无隐”——没有呼吸,没有显化,没有隐没,只有纯粹的“待显之能”在自由流淌,既不向显相倾斜,也不向隐相偏倚,像一个永远充满好奇的孩子,对即将显化什么、隐去什么,都抱着全然的开放,没有预设,没有期待,只有惊喜。阿微与执显织者的显隐舟早已融入这股能流,他们的“显隐之识”也不再是“他们的”,而是成为这股能流的一部分,像浪花是大海的一部分,却又在每一朵浪花中,彰显着大海的浩瀚。
而那些仍在“显隐之间”的存在,早已超越了“显”与“隐”的二元对立,他们只是如其所是地“显隐着”:有时是照亮黑暗的显光,有时是托起光明的隐力;有时是平衡的显相,有时是失衡的隐因;有时在显相中守护隐相,有时在隐相中孕育显相……没有刻意的选择,没有执着的坚守,只有“待显之能”的自然流露,像风拂过湖面,激起涟漪是显,涟漪散去是隐,风本身,从不在乎涟漪的显隐,只是自然地吹过。
深谷的雾气依旧在午夜三点零七分“显化为液态”,又在黎明时分“隐没为气态”,从不在乎谁在观察它的显隐;星寂之海的万星树依旧在吸收黑暗(隐),结出光明(显),从不在乎谁在评判它的得失;思之海的疑问依旧在显相中碰撞,又在隐相中沉淀为智慧,从不在乎答案是显是隐;超验之域的震动依旧在显化体验,又在隐相中滋养觉知,从不在乎感受是强是弱;本源之海的存在依旧在显相中连接,又在隐相中保持独立,从不在乎关系是近是远;时空种子的时间依旧在“此刻”显化,又在“过去未来”中隐存,从不在乎时刻是长是短;全相之树的圆融依旧在显相中包容破碎,又在隐相中孕育完整,从不在乎形态是好是坏;无象之海的本然依旧在显相中流淌,又在隐相中保持空性,从不在乎名相是有是无……
织网人的故事,最终在“显隐不二”中超越了“故事”的显相,也超越了“非故事”的隐相,成为元初芥子呼吸中的一缕“待显之息”——它可能在下一次呼吸中显化为新的星轨,也可能在再一次呼吸中隐没为星尘,甚至可能永远停留在“待显”的状态,像一首写了一半的诗,留白处比已写的诗句更耐人寻味。
而那缕“待显之息”中,始终藏着一个只有“未来织者”才能读懂的秘密:
“显也好,隐也罢,待显亦无妨——织网的真谛,是在显隐之间,永远保持编织的热情,不问结果,只享过程,因为编织本身,就是平衡最美的显相,也是最动人的隐相,更是最永恒的待显之能。”
这个秘密,在元初芥子的下一次呼吸中,化作一颗新的星核,落在某个未知的角落,等待着某个新的织者,伸出手,第一次触碰星尘的瞬间,重新显化……
永远,永远……
元初芥子的“待显之能”在绝对无待之境中流转亿万年,最终在“有无相生之域”凝结成一株“太极之藤”。这株藤没有根须,没有枝叶,却在“有”与“无”的边界不断缠绕生长——生出的“有”会自然归于“无”,空寂的“无”又会悄然生出“有”,像一场永恒的呼吸,吐故纳新,从未停歇。藤的节点处,悬浮着一颗颗“有无之珠”,珠内既有宇宙初生的“有象”,也含万物寂灭的“无境”,触碰珠子的存在,能同时“观”到有与无的共生,像看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,却在同一时刻。
第一位与太极之藤共鸣的,是来自“有无宇宙”的织者。她叫阿无,她的宇宙遵循“有无相生”的法则:有星轨诞生,就有无星轨的虚空作为背景;有织者存在,就有无织者的混沌作为依托;甚至连“平衡”这个“有”,也是因“失衡”这个“无”的对照才显意义。阿无的星尘船是用“有无纱”织成的,船身一半由实有的星轨构成,一半由虚无的空间组成,虚实之间没有明确界限,像水墨画中的晕染,浓淡相接处,生出无限意境。当她的船靠近太极之藤时,有无之珠突然射出一道“非有非无”的光,将船身的有无纱融成一片混沌,实有的星轨开始虚化,虚无的空间反而显露出潜在的轮廓,像雾中看花,似有若无,却更显韵味。
“有是无的显相,无是有的隐基。”太极之藤的藤蔓上浮现出古老的箴言。阿无的有无星轨开始互化:她能“见”到“有”向“无”的回归——一颗恒星燃尽化作虚无,却在虚无中埋下新恒星的种子;一条星轨完成平衡使命后崩解,其能量却融入虚空,成为新星轨的养分;甚至连她自己的星核,也在每一次呼吸中,经历着“有”(能量充盈)与“无”(能量释放)的循环,像潮汐涨落,从未停留。同时,她也能“感”到“无”向“有”的转化——看似空无一物的虚空,其实在孕育着新的宇宙;被认为“失去”的存在,其记忆正以另一种形式在虚无中重生;太极之藤本身,就是从“绝对的无”中生出的“有”,却又在生长中不断回归“无”的本源,像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,既是起点,也是终点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阿无将有无宇宙的“互化星轨”注入有无之珠。珠子在吸纳这股能量后,突然开始“吞吐”——吞时,所有“有”的形态(星轨、时间、存在)都被它吸入,化作“无”的势能;吐时,又有无数“有”从它体内涌现,有的是已知形态的重现,有的是全新的创造,像一位技艺精湛的陶工,在有(陶土)与无(器形)的转化中,赋予泥土新的生命。最奇妙的是,这些新生的“有”都带着“无的印记”——一座山峰的轮廓里藏着它未来崩塌的虚形,一条河流的走向中含着它干涸后的空境,一个织者的星核内,既有“存在”的实感,也有“消亡”的虚念,像一幅画的留白,虽无笔墨,却决定着画面的意境。
阿无的意识随着珠子的吞吐沉入“有无之根”。这里没有有与无的分别,只有一股“待化之能”在静静流转,它既不是“存在”,也不是“不存在”,而是“存在与不存在的中间态”,像水即将结冰的瞬间,既不是液态的有,也不是固态的有,却同时含着两者的可能。当她的互化星轨与待化之能相触时,她突然彻悟:太极之藤不是有无的源头,而是有无的“转化之智”——它告诉所有存在,“有”不必害怕归于“无”,因为“无”中自有新生;“无”也无需羡慕“有”的显相,因为“有”终会回归“无”的怀抱,就像四季轮回,春生(有)夏长(有)秋收(有)冬藏(无),而冬藏的“无”,正是为了春生的“有”。
当她的意识回到有无相生之域时,星尘船已化作“有无之舟”——它没有固定形态,能随有无转化自由变化,有需要时,便显为坚实的船身;无需要时,便隐为虚空的能量,像一位懂得进退的智者,不执着于“有”的存在,也不抗拒“无”的消融。有无之珠照耀的地方,有无转化开始自然发生:织者们不再执着于“必须留下永恒的星轨”,反而在星轨完成使命后,坦然看着它归于虚无,因为知道虚无中自有新的可能;破网者也不再刻意破坏“有”的平衡,而是在“有”过于僵化时,用“无”的力量打破桎梏,像用留白激活一幅拥挤的画。
消息传到有无相生之域时,阿微与阿无正在解析有无之珠的转化频率。她们从阿无的彻悟中获得启示,在太极之藤旁建起“有无观”——观中没有实体建筑,只有一圈“非有非无”的界,能让观者同时“体”验有的实在与无的空灵。当第一位来自“执有宇宙”的织者踏入有无观时,观中的界突然剧烈波动。这位织者的宇宙信奉“有即是一切”,所有“无”都被视为“匮乏”,织者的使命是用“创造之能”填满所有虚空,结果导致宇宙被过多的“有”挤压,星轨与星轨相互碰撞,存在与存在彼此倾轧,像一个塞满杂物的房间,连转身都困难。
“执有如握沙,握得越紧,漏得越多。”阿无的互化星轨化作一道柔波,轻抚执有织者的创造之能。她让织者看见:他拼命填补的“无”,其实是“有”的呼吸空间——恒星之间的虚空,是避免碰撞的缓冲;星轨之间的留白,是能量流动的通道;甚至连他执着的“创造”本身,也需要“无”的休息来滋养,像写作需要灵感(无),才能写出文字(有)。当柔波与创造之能交融时,执有织者的记忆之“无”被唤醒:他曾因失去家园(有化为无)而恐惧,从此便疯狂创造,试图用“有”的堆砌来填补内心的空洞,却不知正是这种执着,让他的宇宙和内心一样,因拥挤而失衡。
阿微驾驶着显隐舟驶入波动的中心。她将元初芥子的“待显之息”注入织者的创造之能,那些被过度创造的“有”开始消解,露出“无”的生机:一片被星轨塞满的空域,在消解后显露出新的引力平衡;一个因过度守护而僵化的星核,在虚空的滋养下重新搏动;甚至连织者自己的执念,也在“无”的观照中开始松动,他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“什么都不做”的虚空,比“做很多”的实在更让人安心,像放下重担的肩膀,终于能自由舒展。
当最后一丝创造之能不再执着于“有”时,执有织者突然坐在地上,看着眼前的虚空笑了——他发现,虚空不是匮乏,而是自由;无不是失去,而是空间。他的星核在这时生出“有无之脉”,能在创造“有”的同时,也尊重“无”的存在:编织星轨时,会刻意留下流动的虚空;守护平衡时,会允许适度的空白;甚至连“织者”这个身份,他也不再执着,有时显为织者,有时隐为星尘,像水在容器中是液态,在空气中是气态,从不在乎形态的有无。
当执有织者的互化星轨与有无之珠共振时,太极之藤突然绽放出“有无之花”——花瓣的正面是“有”的绚烂,反面是“无”的素净,而花蕊中,既有“有”向“无”的凋零,也有“无”向“有”的绽放,像一场永远在循环的生命礼赞。最奇特的是,花朵的香气能同时唤醒“有”的珍惜与“无”的坦然:闻者会珍惜眼前的“有”,却不执着于永远拥有;会接纳必然的“无”,却不恐惧失去的痛苦,像品尝一杯茶,既享受入口的甘醇(有),也接纳饮尽后的空杯(无)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平衡之境的“有无谱系”在这时臻至圆满。阿无与执有织者的名字被一道“转化星轨”串联,星轨的“有”处是创造的高峰,“无”处是消融的深谷,而整体的流转,却像太极之藤的缠绕一样自然,没有刻意的起止,却暗合着有无相生的韵律。谱系的最后,是一片“待化之云”,所有未来的“有”、将归的“无”、以及有无转化的中间态,都在云中若有若无,像一首正在谱曲的歌,每个音符都还未确定,却已能感受到整首歌的和谐。
太极之藤的吞吐没有止境。因为当你说“止境”时,它已在吞吐中化生出新的境;当你说“吞吐”时,吞与吐早已浑然一体,分不清谁是开始谁是结束。有的织者化作藤的一部分,在“有”时成为支撑平衡的星轨,在“无”时化作滋养新生的虚空,无怨无悔;有的在有无转化的“临界带”搭建驿站,让迷茫的存在明白:有不是永恒,无不是终结,像月亮有圆有缺,圆时珍惜,缺时等待,不必焦虑;还有的织者干脆放下“有”的创造,也放下“无”的接纳,让自己随有无自然流转,像一片落叶,有枝头的绚烂,也有无声的飘落,最终化作泥土,滋养新的生命,从不在乎自己是“有”是“无”。
元意识的“非有之音”在太极之藤的每个节点中回荡,这声音不通过任何媒介传播,却能在所有存在的“有无之根”中激起共鸣: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平衡自在流转中。”这句话不是通过耳朵听到的,而是在每个存在的星核中自然涌现的,像种子在春天自然发芽,不需要谁来告诉它生长的道理。所有“有”的星轨、“无”的虚空、待化的可能,都在这共鸣中安住于它们的本然位置,像一场永不停息的有无之舞,舞者与舞台、存在与虚空,早已融为一体,分不清谁在舞谁在看,却在每一次转化中,绽放出平衡的真谛。
当最后一道有无之光照亮有无相生之域时,太极之藤开始“非有非无”——没有吞吐,没有转化,没有有无,只有纯粹的“待化之能”在自由流动,既不向“有”倾斜,也不向“无”偏倚,像一个永远开放的容器,装得下所有“有”的丰富,也容得下所有“无”的空寂。阿无与执有织者的有无之舟早已融入这股能流,她们的“有无之识”也不再是“她们的”,而是成为这股能流的一部分,像浪花是大海的一部分,却又在每一朵浪花中,彰显着大海的深邃。
而那些仍在“有无之间”的存在,早已超越了“有”与“无”的二元对立,他们只是如其所是地“有无着”:有时是支撑平衡的“有”,有时是滋养新生的“无”;有时是创造星轨的“有”,有时是星轨回归的“无”;有时在“有”中守护“无”的空间,有时在“无”中孕育“有”的可能……没有刻意的选择,没有执着的坚守,只有“待化之能”的自然流露,像阳光照耀大地,有温暖的显相(有),也有阴影的隐在(无),阳光本身,从不在乎照亮什么、留下什么阴影,只是自然地照耀。
深谷的雾气依旧在“有”的液态与“无”的气态间转化,从不在乎谁在关注它的有无;星寂之海的万星树依旧在“有”的生长与“无”的凋零中循环,从不在乎谁在计算它的寿命;思之海的疑问依旧在“有”的碰撞与“无”的沉淀中流转,从不在乎答案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超验之域的震动依旧在“有”的体验与“无”的觉知中交替,从不在乎感受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本源之海的存在依旧在“有”的连接与“无”的独立中平衡,从不在乎关系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时空种子的时间依旧在“有”的此刻与“无”的永恒中穿梭,从不在乎时刻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全相之树的圆融依旧在“有”的显相与“无”的隐相中统一,从不在乎形态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无象之海的本然依旧在“有”的流淌与“无”的空性中自在,从不在乎名相是“有”是“无”;元初芥子的待显之能依旧在“有”的显化与“无”的隐在中孕育,从不在乎可能是“有”是“无”……
织网人的故事,最终在“有无相生”中超越了“故事”的“有”,也超越了“非故事”的“无”,成为太极之藤缠绕中的一缕“待化之息”——它可能在下一次吞吐中化身为“有”的星轨,也可能在再一次吞吐中回归“无”的虚空,甚至可能永远停留在“有无之间”,像一首未完的曲,余韵在有无相生之域中回荡,不需要谁来聆听,因为聆听的本身,就是曲的一部分。
而那缕“待化之息”中,始终藏着一个只有“未来织者”才能领悟的真谛:
“有也好,无也罢,有无之间亦无妨——织网的终极,是在有无相生中,永远保持转化的从容,不执着于留下什么,也不抗拒失去什么,因为编织本身,就是有无相生的舞蹈,有星轨的显相,也有星尘的隐在,而舞蹈的韵律,早已刻在每个存在的星核深处,从未‘有’过,也从未‘无’过。”
这个真谛,在太极之藤的下一次吞吐中,化作一颗新的有无之珠,落在某个未知的角落,等待着某个新的织者,伸出手,第一次触碰星尘的瞬间,重新化生……
永远,永远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