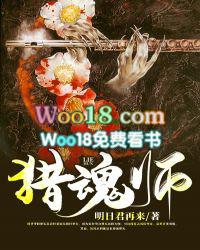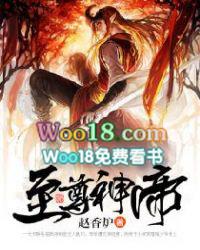六九小说网>循规蹈矩能叫重生吗? > 311 别样偏爱(第2页)
311 别样偏爱(第2页)
中午时分,第一批“种子导师”开始试运营教学课程。云南来的杨春梅教大家做傣味舂鸡脚,一边捶打配料一边讲述女儿的故事:“她瘫痪后脾气很差,摔碗砸筷子。有一次我端上这道菜,她尝了一口,突然哭了。她说,‘妈,这是我八岁那年你说要给我做的,你记得。’”
教室里一片静默。有人低头擦眼泪,有人悄悄录下她的每一个步骤。
与此同时,东北的赵老师带着几位学员复刻“酸菜炖白肉”。她坚持要用铁锅,说铝锅炖不出魂。“老伴最爱坐在炕头喝这汤,一边喝一边骂我咸了,其实每次都舔干净碗底。”她说着笑起来,眼角却有泪滑落,“现在我炖多了没人吃,就分给邻居。他们说,这味儿够冲,够劲,像东北人的心。”
杜佳诺站在走廊尽头听着,心口发烫。她忽然意识到,这些女人带来的不只是菜谱,更是她们一生的情感压缩包??每一道菜背后,都藏着一段无法言说的痛,一种倔强的抵抗,一份不肯熄灭的爱。
下午三点,一位陌生老人拄着拐杖走进食堂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军功章。他在“母亲之墙”前站了很久,最后颤抖着手指抚过“李桂芳”三个字。
杜佳诺认出他是李桂芳的丈夫??那位曾在贵州山区支教三十年的老教师。新闻里提过,他因中风半身不遂,早已无法远行。
“您……怎么来的?”她快步上前搀扶。
老人声音沙哑:“坐了三天火车,换两次车。我想看看她……留下的东西。”
杜佳诺带他来到专属座位区,泡了一杯热茶,又端上一碗刚出锅的酸汤鱼。老人看着红亮的汤面浮着野葱花,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勺。他舀了一小口,闭上眼,良久,泪水顺着眼角沟壑淌下。
“她……终于被人知道了。”他喃喃道,“一辈子围着灶台转,别人说她没出息。可你看,她的味道,走到了长沙。”
杜佳诺蹲在他身边,轻声说:“不止长沙。下个月,深圳、成都、西安都会有‘妈妈的味道’。您愿意……替她去讲一次课吗?就讲这道酸汤鱼,讲她是怎样一个女人。”
老人睁开眼,目光浑浊却坚定:“我讲不了太多话,但我可以……写下来。用左手。”
当晚,杜佳诺收到一封手写信,字迹歪斜却用力深刻:
>“我妻子李桂芳,
>不识几个字,
>却教会了十里八乡的女人做菜。
>她说,饿肚子的孩子不会哭,
>会缩在角落发呆。
>所以她每天多煮一锅饭,
>放在门口石墩上。
>后来有人说她是‘疯婆子’,
>可那些孩子长大后,
>都管她叫‘干妈’。
>
>她没想过有一天,
>她的名字会被刻在墙上。
>但她一直相信:
>一口热饭,
>能救一个人的命;
>一道家常菜,
>能暖一个人的心。
>
>请替我告诉她:
>你做到了,老婆子,